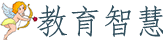我在监狱的院于里干了两天苦工。那是个重活,虽然我一有机会就装病,我还是给搞垮了。这是因为伙食的关系。谁也不能靠那种伙食干重活。面包跟水,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一切。照说,我们一星期应当吃一次肉;可是,这种肉总是不够分配,而且它又得先用来煮汤,煮得一点养分也不剩,因此,一个星期里能不能尝到一次。并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这种面包跟水的伙食,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们得到的水很多,面包却老是不够。一份面包只有两个拳头那么大,每个犯人每天只能得到三份。至于水,那我可一定要说,它的确有一桩好处——挺热。早上,它叫做“咖啡”,中午,它就很神气地成了“汤”,晚上,它又会化装成“茶”。其实,从早到晚,照旧还是那种水。犯人们都把它叫做“邪水”。早晨,它是黑水,颜色是用焦面包屑煮出来的。中午,它就去掉这种颜色,加上一点盐和几滴油。开晚饭的时候,它又换上一种无论怎么也猜不出的发紫的赭石色;这是一种糟透了的茶,不过倒是真正的热水。
我们这伙人全是伊雷县监狱里的饿汉。只有“长期犯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吃饱。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伙食跟我们“短期犯人”的一样,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全会饿死。我知道那些长期犯人吃得要充足一点,因为我们大厅底层有一整排牢房都住的是这种家伙,我在当杂役的时候,常常借着送饭偷他们的伙食。一个人要是单吃面包而又吃不够,是活不下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