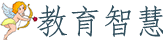开往纳伊的小火车刚驶过玛约门,正沿着通往塞纳河岸的林荫大道行驶。小车头拖着它那节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碍事的行人车辆,像一个气喘吁吁的长跑者,喷吐着蒸汽;活塞像是匆匆运动着的铁腿,发出嗑嗵嗑嗵的响声。夏日傍晚的闷热笼罩着路面;虽然一丝风也没有,还是扬起阵阵白色的尘土,石灰似的,浓浓的,呛人的,而且热烘烘的。这尘土粘在人们湿漉漉的皮肤上,迷住人们的眼睛,甚至钻进人们的肺里。
大道两旁,不少人走到户外来透透气。
车窗的玻璃都放了下来;车子开得很快,所有的窗帘都在飘舞。只有寥寥几个人坐在车厢里(在这样的大热天,人们更喜欢待在车的顶层或平台上)。其中有几个装束格调不怎么雅致的胖太太;这些郊区的中产阶级妇女,缺乏高贵的风采,去傲慢得不合时宜。还有几个在办公室辛劳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的男士,脸色蜡黄,弓腰缩背,因为常年伏案工作,看上去一个肩膀有点高。从他们焦虑不安、愁眉不展的面孔,就知道他们家庭生活中烦恼重重,经常手头拮据,昔日的希望已经注定成为泡影。他们全都属于那支落魄潦倒的穷鬼的大军,在巴黎周边近乎垃圾场的田野上,在石膏抹灰的单薄的房子里,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门外的一小块花坛就是他们的花园了。
紧挨着车门,一个矮胖的男子,面颊有些浮肿,肚子垂在叉开的两腿中间,穿一身黑色衣服,挂着勋章绶带。他正在跟一位先生聊天。对方身材瘦长,不修边幅,穿着肮脏的白色亚麻布衣服,带一顶陈旧的巴拿马草帽。前一位是海军部的主任科员卡拉旺先生,说起话来慢慢腾腾,吞吞吐吐,有时候简直就像个结巴。后一位曾经在一条商船上当过卫生员,最后在古尔波瓦圆形广场附近安顿下来,用他一生走南闯北仅剩的似是而非的医学知识,在当地贫苦居民中间行医;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医生”。关于他的品行,很有些流言蜚语。
卡拉旺先生一向过着标准的公务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每天早上守常不变地去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赶去办公的相同的脸;每天晚上他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见他亲眼看着变老的相同的脸。
他每天在圣奥诺莱城厢街拐角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又去买两个小面包,然后就走进部里,那神情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办公室。他总是惴惴不安,时刻都在担心自己有什么疏忽,会遭到申斥。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能改变他单调的生活规律;因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级和奖金,他对什么都不关心。不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已经不计较什么嫁妆,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他从来不谈公务以外的事。他被那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缩了的脑子里,除了和部里有关的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思想、希望和梦想。不过这个科员想起一件事总是愤愤不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有银线饰带而被人称作“白铁匠”的,一调进部里就能当上副科长或者科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在饭桌上,当着与他同仇敌忾的妻子,有根有据地论证:把巴黎的官职给那些本应该去漂洋航海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极不公平。
他现在已经老了。可是他竟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一生是怎么过去的,因为他出了中学大门就直接跨进了办公室,只不过从前望而生畏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一看见这些衙门暴君的门槛,他就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在人前总显得窘迫不安,和人说话总是低声下气,甚至紧张得口吃,就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恐惧心理所致。
他对巴黎的了解,并不比一个每天牵着狗到同一家门口讨饭的瞎子更多。即使在他那一个苏一份的报纸上读到什么大事或者丑闻,他也认为都是凭空杜撰的故事,编出来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是个秩序的拥护者,保守派,虽无一定的政见,但敌视一切新鲜事物的保守派。凡是政治新闻他都略过不看,何况他那份报纸拿来某一方的钱,总是为满足该方的需要而对新闻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着香榭丽舍林荫道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就像是人生地疏的旅游者彷徨在遥远的异乡。
就在今年,他完成了按规定所必须的三十年的服务。1月1日那天,他获得了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在这些军事化的机关里,就是用它来奖励那些被钉在绿色卷宗上的犯人,奖励他们漫长而又悲惨的苦役(或者美名其曰“忠诚服务”)的。这个意外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出于对自己所属的“勋位团”理所当然的礼貌和尊重,从那以后,他就取缔了杂色的长裤和式样花哨的上衣,只穿黑裤子和更适合佩戴他那宽宽的“勋章绶带”的长礼服;他每天早上都要刮脸,仔细清洁护理手指甲,并且每两天就换一件衬衫。总之,转眼之间,他就变成了另一个卡拉旺,整洁,庄重,而且待人接物还颇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
在家里,他说什么都要扯上“我的十字勋章”。他甚至骄傲到了如此程度,对别人在扣眼上扣的任何一种勋章都无法容忍。他见了外国勋章尤其怒不可遏——“这种勋章根本就不应该允许在法国挂出来”。他特别看不惯舍奈“医生”,因为每天晚上在小火车上遇见他,他,他总是挂着一条不三不四的勋章绶带,有白的,有蓝的,有橙黄的,还有绿的。
从凯旋门到纳伊的这段路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仍是老生常谈。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们先涉及的是地方上的种种弊端;他们对这些弊端都很反感,可是纳伊市的市长却偏偏不闻不问。接着,正像和医生做伴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卡拉旺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指望通过闲谈的方式捞到些许免费的指点,甚至是一次诊断呢,只要做得巧妙,别让他看出破绽。再说,他母亲的情况近来让他十分担心。她常常昏厥,好久才能醒过来。虽然九十高龄了,可是她就是不同意去看病。
卡拉旺一提到母亲的高寿,就心情激动。他一再地对舍奈“医生”说:“活这么大岁数的人,您常见吗?”说罢,他就深感幸运地搓搓手,倒不是他希望看见老太太在世上没完没了地活下去,而是因为母亲寿命长也是他本人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嘿嘿!我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事故,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卫生员怜悯地看了他一眼;他在转瞬间端详了一下对方通红的脸、肥肥的脖子、坠在两条松软的粗腿之间的大肚子,以及这虚胖的老职员容易中风的浑圆的身坯;然后,他一只手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白色巴拿马草帽,冷冷一笑,回答:“未必吧,老兄,令堂瘦得皮包骨,而阁下呢,胖得像个汤桶。”卡拉旺被他说得心慌意乱,哑口无言。
好在这时候小火车到站了。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请他到对面他俩经常光顾的环球咖啡馆喝杯苦艾酒。老板和他们是朋友,向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隔着柜台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走过去,找从中午起就坐在那张桌上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迷。他们互相热情地打了招呼,并且问了那句少不了的“有什么新闻呀”,然后打牌的人继续打牌,他俩就告辞出来。他们头也不抬,只是伸出手来互相握了一下,便各自回家吃饭。
卡拉旺住在古尔波瓦广场附近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楼下是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个卧室、一个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过的椅子根据需要从这边屋子搬到那间屋子。卡拉旺太太把时间都花在打扫卫生上。她的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斯和九岁的儿子菲利普-奥古斯特跟邻里的孩子们在大街边的阳沟里游戏。
卡拉旺把母亲安置在楼上。老太太的小气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而她又长得瘦骨嶙峋,所以人们都说:天主把她精打细算的原则都用在她身上了。她总是心情恶劣,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发脾气。她经常隔着窗户,冲着站在门口的邻居、卖菜小贩、清道夫和儿童破口大骂。为了报复她,她出门的时候,孩子们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大叫:“老——妖——精!”
一个粗心得叫人难以相信的诺曼底来的小女佣,给他们家做家务活。为了预防意外,她睡在三楼,老太太旁边。
卡拉旺回到家的时候,他那爱洁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布擦那几把分散在几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的桃心木的椅子。她总是戴着绒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那便帽缀有五彩缎带,还老往一边耳朵上滑。每逢有人撞见她上蜡、刷呀、擦呀、洗呀,她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不过我也有奢侈的地方,那就是清洁,它跟别的奢侈同样有价值。”
她生来就讲究实际,而且固执己见;在一切事情上她都是丈夫的向导。每天晚上,在饭桌上,然后在床上,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办公室里的事,虽然他比她小二十岁,他却像对神父似的对她无所不谈,并且不论什么事都遵从她的意见。
她压根儿就不曾漂亮过,现在更丑,矮小又干瘦。她那不多的女性特征,本来还是可以巧妙地显露一二的,但她偏偏对着装一窍不通,也就被永远埋没了。她的裙子好像总往一边歪,无论什么场合,哪怕在大庭广众面前,她也常常在自己身上抓抓搔搔,几乎成了一种怪癖。她容许自己所做的唯一装饰,就是平时在家戴的便帽上缀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丝带,自以为很美。
她一瞧见丈夫回来,就直起腰,吻着他的颊髯,问:“我的朋友,你想着去波丹了吗?”(这话指的是他答应替她办的一件事。)他听了马上垂头丧气地倒在椅子上;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把这事儿忘了。他说:“真是邪了门了,我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可是没用,到了傍晚还是忘了。”见他很难过,她就安慰道:“你明天记住不就完了。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有,还是一件大新闻呢:又有一个‘白铁匠’被任命为副科长。”
她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问:“哪个科?”
“对外采购科。”
她气呼呼地说:“这么说,是拉蒙的那个位置了,正好是我希望你得到的那个位置。拉蒙呢?他退休了?”
他喃喃地说:“退休了。”
她立刻暴跳如雷,便帽一直滑到肩膀上:“完了!你看,这个破地方,现在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波纳索。”
她拿起总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查找,念道:“波纳索。土伦。1851年出生。1871年任见习军需官。1875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听到这句问话,卡拉旺心里雨过天晴。他乐得肚子直抖。“跟巴兰,他的科长巴兰,正好是一路货色。”接着,他就开怀地笑着,讲起他那个部里人全都觉得精彩的老笑话:“千万别派他们从水路去视察黎明军港,他们乘观光小火轮也会晕船呢!”
不过,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板着脸。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搔着下巴,咕哝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个有交情的议员就好了!只要议会知道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部长立马就会垮台……”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的吵嚷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斯和菲利普-奥古斯特从阳沟那儿玩耍回来了,他们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步步为营,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他们的母亲横眉怒目地冲了出去,一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使劲地摇晃着他们,把他们推进屋里。
他们一看见父亲就连忙向他扑过去。他慈祥地吻他们,吻了很久,然后坐下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跟他们说说话儿。
菲利浦-奥古斯特是个小淘气,头发乱糟糟的,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干净,脸上一副白痴相。玛丽-路易斯长得像她母亲,说话也像她,张口就像在重复她的话,甚至连手势也跟她一模一样。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呀?”他开心地回答:“宝贝女儿,你那位每个月都要来咱家吃饭的朋友拉蒙就要离开我们了。有个新来的副科长接了他的位置。”她抬起头,望着父亲,用早熟的孩子才有的那种体恤的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从你背上蹿上去了?”
他敛起笑容,没有回答;然后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窗户的妻子:“妈妈在楼上好吗?”